全部還要從1949年說起,意大利于該年成為北大西洋公約安排的開創成員,這不僅僅在軍事上成為了美國的盟友,也等于必定了美式的經濟開展辦法。緊接著,這座亞平寧半島上的文藝復興搖籃,在1952年和1957年相繼成為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開創成員,遵從著馬歇爾計劃的腳步,開端了本國的戰后經濟復蘇。但是快速前進的浮華之下,卻埋著社會矛盾的引線,出生于1949年的弗蘭科·貝拉爾迪或許也無法幻想,最總算1968年迸發的工人/學生運動,會影響了他終身的學術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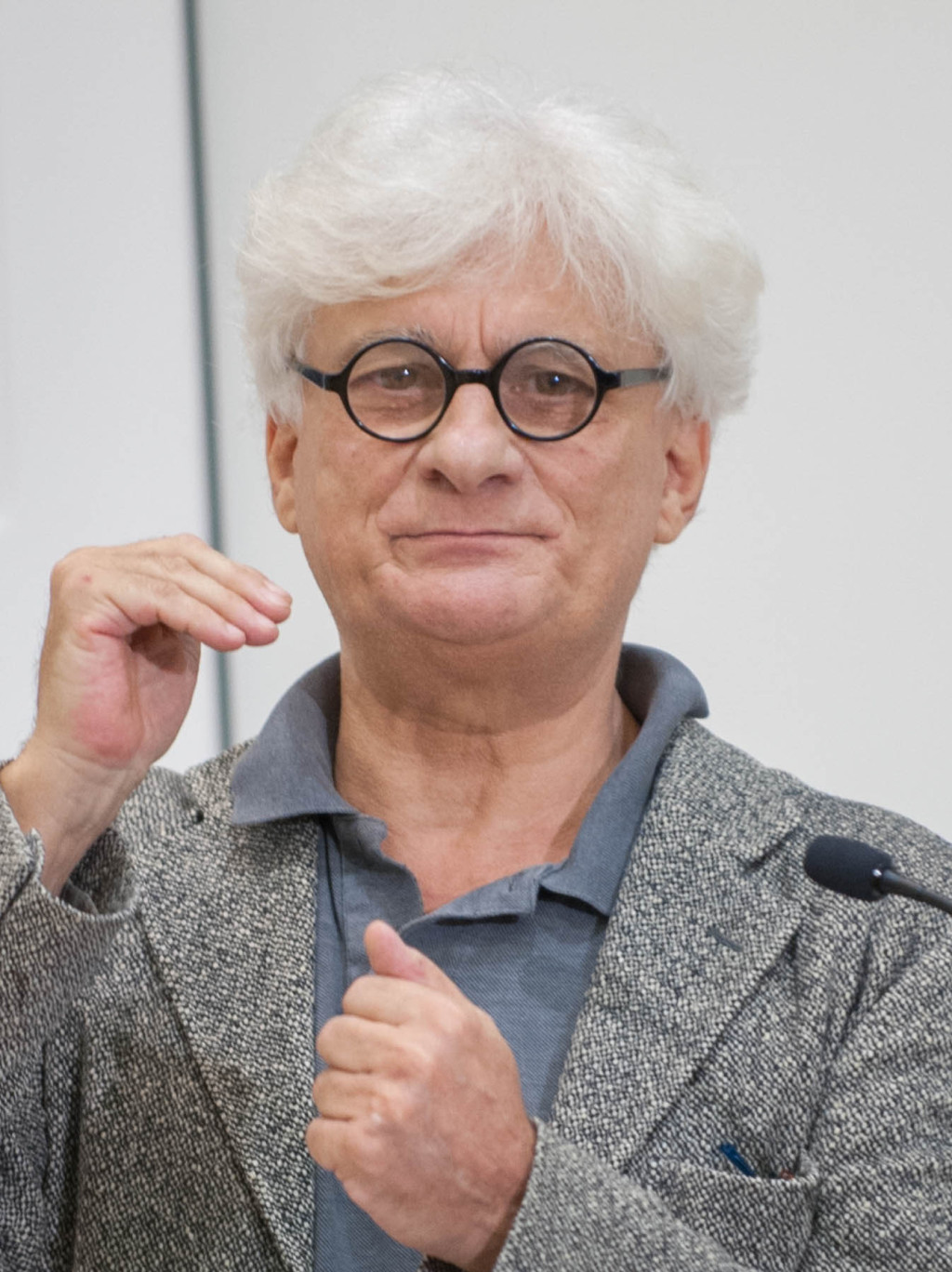
弗蘭科·貝拉爾迪
相較于弗蘭科·貝拉爾迪,“比弗”(Bifo)這個自學生年代起就運用的簽名更為群眾所熟知。或許他在剛參加意大利工人主義安排,并投身1970年代“熾熱之秋”運動時,還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名年青的社會運動者會有何種的風險。1970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敵對作業》(Contro il lavoro)不過便是連續了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實在要挾到他本身安全的,則是他于1975年和1976年別離創建的地下刊物《穿/越》(A/traverso)以及意大利首個海盜電臺阿麗切(Radio Alice)。從此,傳媒技能與社會運動的聯絡成為了他思維與舉動的中心。1977年該電臺被逼封閉,而比弗也因“經過播送鼓動暴亂”在博洛尼亞被警方通緝,所以他被逼流亡巴黎,并在此結識了菲利克斯·加塔利與米歇爾·福柯。盡管之后返回過祖國,但比弗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便移居美國紐約,為當地還有米蘭的雜志撰稿。
作為社會活動參與者,比弗造訪了國際各地,從印度到墨西哥、尼泊爾,乃至中國都留下了他的腳印,在與各類媒體的不同觸摸中,他的左翼理論愈加深化地觸及了精力分析、賽博朋克以及當代藝術與未來等多種主題。而南京大學出書社于2025年7月出書的《魂靈在作業:從異化到自主》,則是比弗本身理論研究的經典代表作。他在標明本錢主義是怎么使用新式手法,對人類的身體與精力進行持續克扣的一起,也沒有忘記自己作為工人主義思維家該有的人文關心。可了解了魂靈為何以及怎么在作業的底子原因,就真的能找到通往自在的解放之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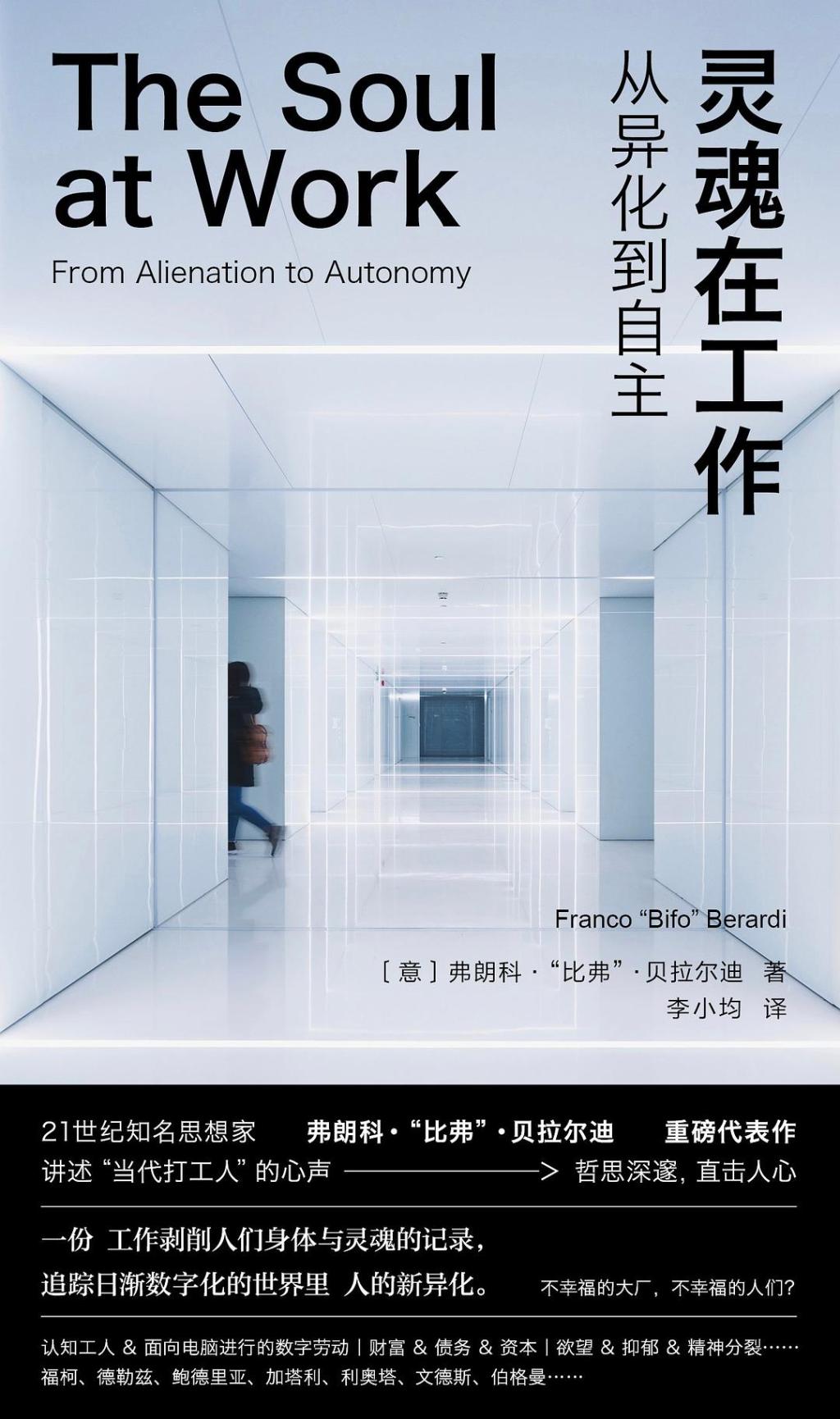
《魂靈在作業:從異化到自主》書封
一些比弗引證的概念
首先是“魂靈”,盡管比弗一向遵從著馬克思主義,但他依然像一切思維家相同,會回到古希臘時期去尋覓最原初的概念,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的唯物主義讓他確認了魂靈的含義——“魂靈是有生命的氣味,把生物性的物質轉化為生命性的身體。”(本書前語第1頁)所以魂靈與身體組成了有糾纏的共生聯絡,在21克的科學神話被打破之后,魂靈是身體的一個思維器官這種結論,或許能夠讓人文主義者更好地考慮個別與國際的聯絡。
其次便是“知本階層”,馬克思早在1858年的《機器論片段》中就預言了一般智力會成為最主要的出產力,而跟著技能的前進,數字和網絡讓傳統常識分子的相貌面目一新,躍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主體。這個團體所進行的常識勞作,也不再依照傳統的一二三擺放次序,與一般的社會勞作區別開來,而是在空地之地進行著一種重要的焊接作業,保證出產進程和社會溝通的曉暢。知本階層正是在這個進程中成為了認知勞作的社會性肉身,時刻保持著專心,無休止地奉獻著才智。
接下來便是“異化”,盡管唯物主義從底子上是敵對唯心主義的,但并不阻礙比弗以此種觀念來架構“異化”的概念,他模擬了一場青年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論爭,還將薩特和馬爾庫塞也拉了進來,終究將對人類本真性的預設融入進了前史存在中,“異化”現已不只僅是實質的損失、被否定、被掠奪、被暫停,更是人類之間的別離與丟失,是人對物的屈服。
還有“作業”,現在作業所觸及的辦法、環境與條件,和半個世紀前工人階層斗爭時所抵擋的作業辦法現已徹底不相同了,面臨屏幕,手敲鍵盤現已成為了一種遍及趨勢。數字技能更是拓荒了一種勞作的全新視角,手工勞作逐步被執行編程指令的機器代替,腦力勞作則正在發明實在的價值。盡管勞作依然是依托作業內容和薪酬收入,以出售個人時刻為內容的社會活動,但仰仗高科技的各行業從業者,早已不是傳統工業出產線上的工人——盡管作業內容能夠簡化,但卻無法交換。出產線工人在八小時之后,能夠從“暫時逝世”的狀況中復蘇,但高度特異化且深度個性化的作業,卻為現在的作業者們豎起了鞏固的壁壘,而其間永久沒有守時八小時的鬧鐘。
一條比弗串起的草蛇灰線
能夠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工人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最好的繼承者,他們緊捉住“勞作”與“本錢主義”的聯絡,以工人/學生的二元組在進行著抵擋,之所以聯合學生這個團體,或許是由于在工業工人階層看來,他們不只會成為未來的自己,也是行使理性來保證人權、相等和普世法令的常識分子們的雛形。但是這對組合的任何成員都沒有料到,進入新世紀后,本錢主百度網盤在線播放記錄義有了新的對策,工業工人逐步淡出舞臺,常識分子不再是自在個別,而是成為了群眾社會的主體,融入進了一般出產進程。
科技成了本錢的新嘍啰,用各種新穎的辦法代替了單個勞作,傳統工人被降格成為次級出產者,失掉主體位置之后,工人形象好像變為了一具無生命的殘骸。而本錢憑借“企業”完成了一種共和,敵對逐步消失,企業反倒成為了能夠將勞作開展成作業的投資者。作業成功的進程也伴跟著財富的堆集,但是在消費社會的趨勢下,“財富”從身心愉悅的質量,逐步傾向了本錢的經濟學唇舌所給出的答案:財富意味著具有讓咱們能夠消費的手法,即金錢、信貸和權利的或許性。(本書第93頁)這樣一個片面的答案,卻簡直主宰了全國際——人們總想著堆集購買力,卻沒有意識到花費了更多的時刻,而留下來供自己享用的時刻卻越來越少。
在多年與媒體觸摸的進程中,比弗發現社會的神經體系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壓榨:日常日子和人際聯絡逐步匱乏,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化的、符號化的補償。在這種補償中,“夸姣”也改動了滋味,這兩個字逐步有了某種團體性含義,經過廣告進行碎片化的布道,讓人們將自己的愿望投進經濟理論和政治舉動的體系中,而且深信,只要成為顧客,才干終究捉住左躲右閃的“夸姣”。
新自在主義倡議的競賽看似是件功德——每個人都有資歷為本身爭得利益,商場為競賽者們徹底敞開,國家不得過多干涉經濟活動。但是這遮蓋不了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雙眼,比弗確定新自在主義表揚的商場不過便是個神話,經濟歷來無法和權利徹底分隔,外表昌盛的背面不只要暴力和謊話,還帶來了間斷性的金融危機。競賽、商場、自在、危機……這一系列本錢主義的新手法,像一劑毒針,扎入人類的身體,直達呼喊著本真性的魂靈。
即使電影有了聲響,卓別林的《摩登年代》依舊是對工人日子最透徹的藝術表達,上世紀二十年代無聲的機械性動作一向連續至六七十年代。可現在在信息技能的加持之下,言語卻過載了,咱們有必要時時刻刻在線,由于這關乎咱們的作業,作業連接著購買力,而超強的購買力就能夠帶來夸姣——咱們便是這樣深深陷入了線路和屏幕的泥濘之中,逐步扔掉了對隱私的維護,這是一種侵吞,更是攻擊。對物化的屈服在數字光纜的持續鞭撻下,變成了對非實際化的俯首稱臣。
相同的,魂靈對年代性異化的改動也有了不同的反響。當工人們還在重復每天超出八小時的可代替勞作時,魂靈帶領身體抵擋的是出產流程,中止的是本身的勞作,機床停了,鍋爐的氣焰漸逝,火車不再噴出汽笛聲,這時候的工人團體是聯合一致的。而新自在主義帶來的咒語過火悅耳,就連魂靈也投入了作業,它再沒有力氣抵擋引誘,只能氣若游絲地讓身體有些非一般的動作,異化不再是對人類本真性的正告,而是被凄慘地歸為精力病理學,冠上了抑郁癥和精力分裂癥等新姓名。在新的年代,工人階層不復存在,認知勞作者盡管是才智的無產階層,卻如一盤散沙,關于從前高喊共產主義的比弗來說,或許哀極大于此了。
一些比弗看到的期望
作為思維家的比弗先搬來了救兵——歐陸哲學自1970年代起在從頭構建概念的坐標,福柯、德勒茲、阿甘本等,都協助這位身世博洛尼亞的革命者從頭考慮現已變形的權利結構與社會主體。而在一系列后現代的言語之中,鮑德里亞那具有顛覆性的觀念與概念(“仿真”、“內爆”和“災禍”等)不只充滿了理論與政治的內在,還好像白一般,直指當下的現狀。
在鮑德里亞的指導下,比弗確認了實在場景的被扔掉,攝像機、膠片與屏幕讓實在的場景與人進入到仿真的環境之中,蒙太奇成為了支配者,實際則成為了荒漠,屏幕上投射出的,是無休止的符號。在鮑德里亞看來,進入擬真和擬像之后,愿望和力比多被機械化了,但關于這種愿望權利的理論,比弗并沒有茍同,他在德勒茲和加塔利那里找到了更好的解說:愿望是前史的中心范疇,由于百度網盤在線播放記錄在這一范疇內,那些對團體心智的構成、因而也是對社會前進的主軸而言至關重要的力氣,他們經過并置或抵觸在此相遇。(本書第150頁)比弗很好地提取了《反俄狄浦斯》中的辦法,哲學景象中的“無器官身體”讓他看到了主體性成形的進程,佐以社會批評概念的精力分析,也讓他認同了阿蘭·埃倫貝格在《疲于做自己》中所評論的、無法否定的現實:依托競賽的抑郁癥,其實是一種社會病理綜合征。
比弗是個十分優異的理論研究者,他沒有對哲學家們的著作望文生義,而是奇妙地提煉出了可認為己所用的中心部分。當下年代病理的特征是虛擬的愿望目標在無限激增,直播間、購物渠道無時無刻不在用構思十足的廣告宣傳著琳瑯滿目的消費品,身心愉悅的享用一向被延遲,力比多能量逐步干枯。假如屏幕不再閃亮,驚懼就會襲來,對狹小空間的過火重視削弱了人們對本身和別人的了解,或許曩昔人們還試著了解對方,但現在連這弱小的目的也將消失殆盡。
比弗期望現代人能看到新自在主義為社會帶來了怎樣的作用,他引證了福柯的“生命政治”、安東尼奧尼、伯格曼和文德斯的電影著作,他想為群眾深挖這背面的運轉規律,想讓群眾意識到,約束競賽的法令標準和社會規矩看似被消除了,但其實是被簡化了,咱們的日子——包含醫療、教育、性、情感、文明等——都變成了遵從供需規律的經濟空間,現在咱們不只身體被套上了鎖鏈,就連魂靈也已屈服于技能出產。但假如咱們的腳步稍稍慢一些,先放下對消費的追求和對經濟的瘋狂,從頭考慮“財富”的實在界說,或許就能實在認識到,本錢主義歷來沒有被削弱過,它僅僅一次又一次地轉換相貌,讓咱們不斷地跳入勞作與本錢的聯絡漩渦中,使自己忘記了何為享用天然,何為相互合作。只要從“競賽”這個幻象中掙脫出來,本錢主義的根基才會有所不堅定,而人類本真性的自在才有或許浮出水面。
結語
比弗絕不是達觀的,盡管他在本書終究說本錢主義持續五百年的體系終究會潰散,但是這五百年間,人類的經濟觀現已逐步固化,本錢主義面臨各種危機只會越發地稱心如意。在比弗看來,全球經濟潰散是一個時機,人們在曩昔的五個世紀間,為了作業而扔掉了太多,已然社會結構現已變得松懈,不如就趁現在,解開出產過剩的兩層捆綁。他幻想著讓收入脫離經濟學結構,改為人類學結構,而魂靈的自在,能夠依托“美學范式”,讓哲學與藝術進入混沌之中。這樣就能夠使人們愈加重視本身,釋放出常識、才智和情感作為財富的一部分,而非強迫性的無用勞作。不得不說,思維家的展望,確實是既夸姣,又心愛。
當從前的工廠變成了現在的大廠,手中的螺絲刀換成了鍵盤和鼠標,就算有好心人告知那個預備簽署膏火借款合同的年青人,魔鬼僅僅換了副面孔,他就藏在銀行的死后,等著你簽下 “贊助學業”的魂靈契約,可這個年青人還能有更好的挑選嗎?就算咱們都知道996背面的不道德,但關于一個沒有依托、作業困難的學生來說,即使是有縫隙的勞作合同,依然是一份可貴的作業時機。打工人面臨所謂經濟和政治的窘境,或許覺得仍是“干更多的活,賺更多的錢,但別去考慮社會”這種話更悅耳些。當人們的認知水平有所進步,并不會像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工人階層一般,聯合一致,為了進步薪酬和作業環境水平而奮起抵擋,只會是將自己投向下一個作業場域,持續一種深諳此道的“惡性循環”。自在經濟的毒現已太深,深到這種次序底子無法被打破。進入21世紀,比弗仍在高喊“敵對作業”,而他神往的共產主義,也掩蓋上了共和的糖衣,所以他只能將使命轉向構建自主。只不過他也清楚,他從未扔掉的馬克思那“個人的自我完成”和他想象的“高興的獨特化”,現已成為了社會的精力分析醫治進程,而這進程,無盡且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