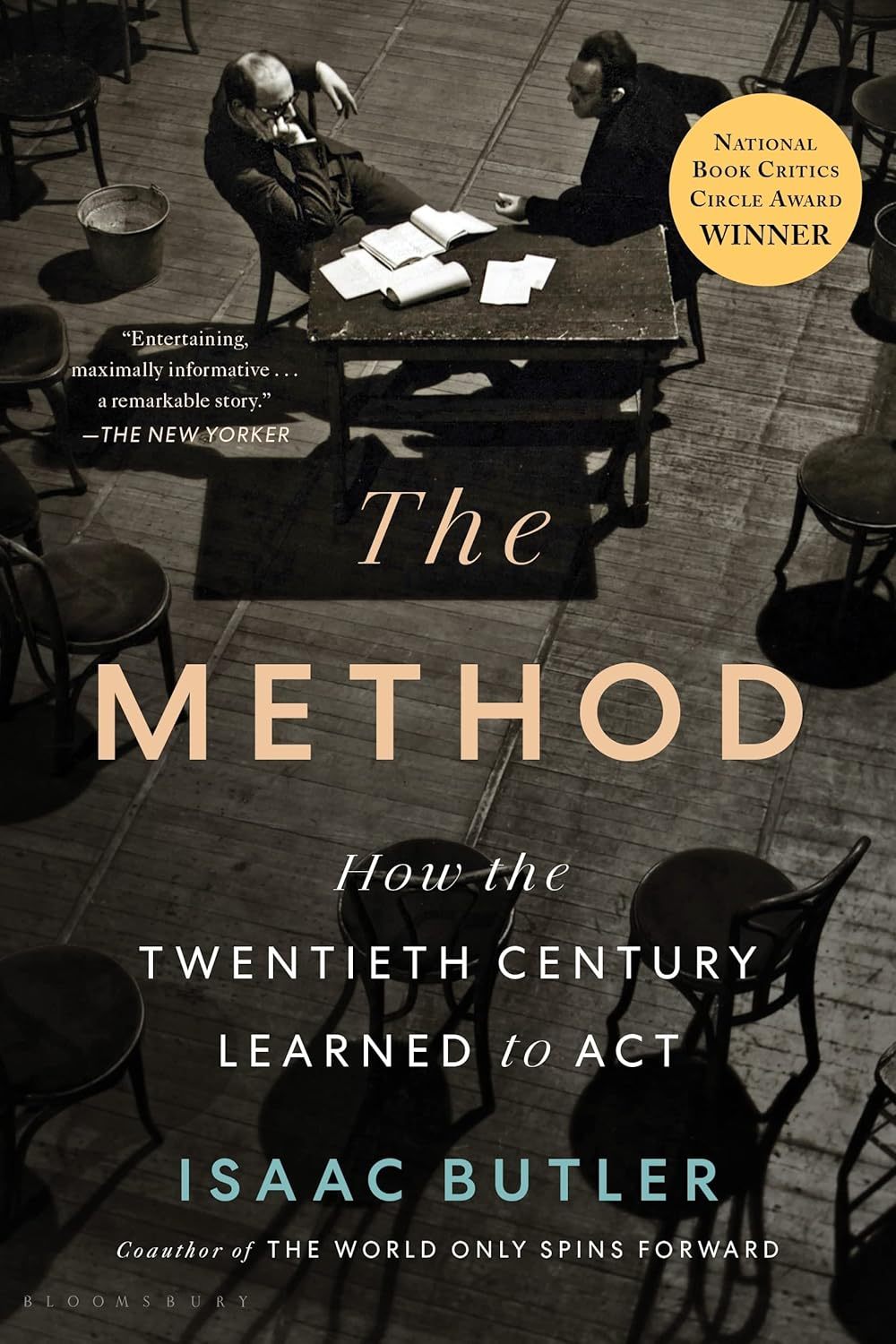
Issac Butler, The Method: How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arned to Act, Bloomsbury, 2022
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到美式扮演“辦法”
作為一名巨大的藝人、導演、戲曲理論家和教育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終其畢生精力,探究藝人怎么描寫人物和發(fā)明人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三部著作中題為“How an Actor Prepares”的一部被翻譯為“藝人的自我涵養(yǎng)”,也讓“自我涵養(yǎng)”這一表到達為長盛不衰的盛行語。扮演作業(yè)的中心,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來,在于將認識進行發(fā)明性的轉(zhuǎn)化,以盡或許靠近人物的心思和人物的心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在幾十年的打開進程中閱歷了兩個階段,從控制藝人的心思狀況和心里國際轉(zhuǎn)向側(cè)重扮演中身體動作的操練。第一階段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操練藝人了解人物的行為動機,第二階段則偏重扮演所需的詳細身體技能。扮演作業(yè)高度依靠藝人的身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旨在協(xié)助藝人把人物的內(nèi)涵狀況經(jīng)過肢體以外化,為特定人物探究一套行為表現(xiàn)辦法,然后完結(jié)藝人用自己的身體活動表現(xiàn)人物的心思活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從俄國傳入美國今后,啟示一大批戲曲扮演藝術(shù)家前仆后繼地進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探究。掌握藝人作業(yè)室(The Actors Studio)的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承繼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打開出獨具一格的“辦法派”扮演風格。從聲名遠揚的集體劇院(The Group)和藝人作業(yè)室走出的扮演藝術(shù)家和藝人操練專家,他們與斯特拉斯伯格求同存異,依據(jù)個別分析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翻開了多樣化、發(fā)明性的實踐。身兼藝人和扮演學者雙重身份的埃塞克·巴特勒(Issac Butler),在其所著《辦法:二十世紀的扮演課》(The Method: How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arned to Act,后簡稱《辦法》)一書中,雄心壯志地出現(xiàn)了扮演風格長達一個世紀的打開進程,其敘說與分析環(huán)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的樹立、演化、傳達以及美國式辦法派扮演風格的嬗變翻開。
在現(xiàn)代主義推翻了自啟蒙運動以降的文學和藝術(shù)傳統(tǒng)這一布景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聯(lián)同無調(diào)性音樂、現(xiàn)代主義修建、籠統(tǒng)派繪畫等——改動了人們的藝術(shù)欣賞和美學品嘗,人們開端注重自我與他者、周遭國際在繼續(xù)互動中生成的閱歷和主體在情感領會、反思性基礎上構(gòu)成的內(nèi)涵國際。《辦法》一書是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掀起的扮演風格革新的社會文化史研討,在巴特勒的前史敘說和分析中,咱們實際上看到不止一種“系統(tǒng)”或許“辦法”,而是藝術(shù)家們針對什么是好的扮演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爭鳴。
領會、動機與心思技能
故事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與聶米羅維奇-丹科欽創(chuàng)立的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開端。在他們?nèi)兆拥哪甏韲鐣⑺嚾丝醋魇俏恢孟沦v的集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出生于家境優(yōu)渥的巨賈階級,從小就對戲曲和扮演感興趣,生長中常常在劇團與藝人打交道。在掌握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做的許多作業(yè)是為了提高藝人的社會位置,他給藝人擬定了一系列的作業(yè)原則,以為藝人要想被當作藝術(shù)家對待,他們首要需求恪守作業(yè)的紀律和作業(yè)的道德。而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經(jīng)過開發(fā)一系列的扮演操練,企圖提高藝人扮演的技能水平。總歸,在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操練和辦理藝人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期望經(jīng)過提高藝人的專業(yè)化程度,讓社會群眾尊重這一作業(yè),起到了推進藝人的作業(yè)化進程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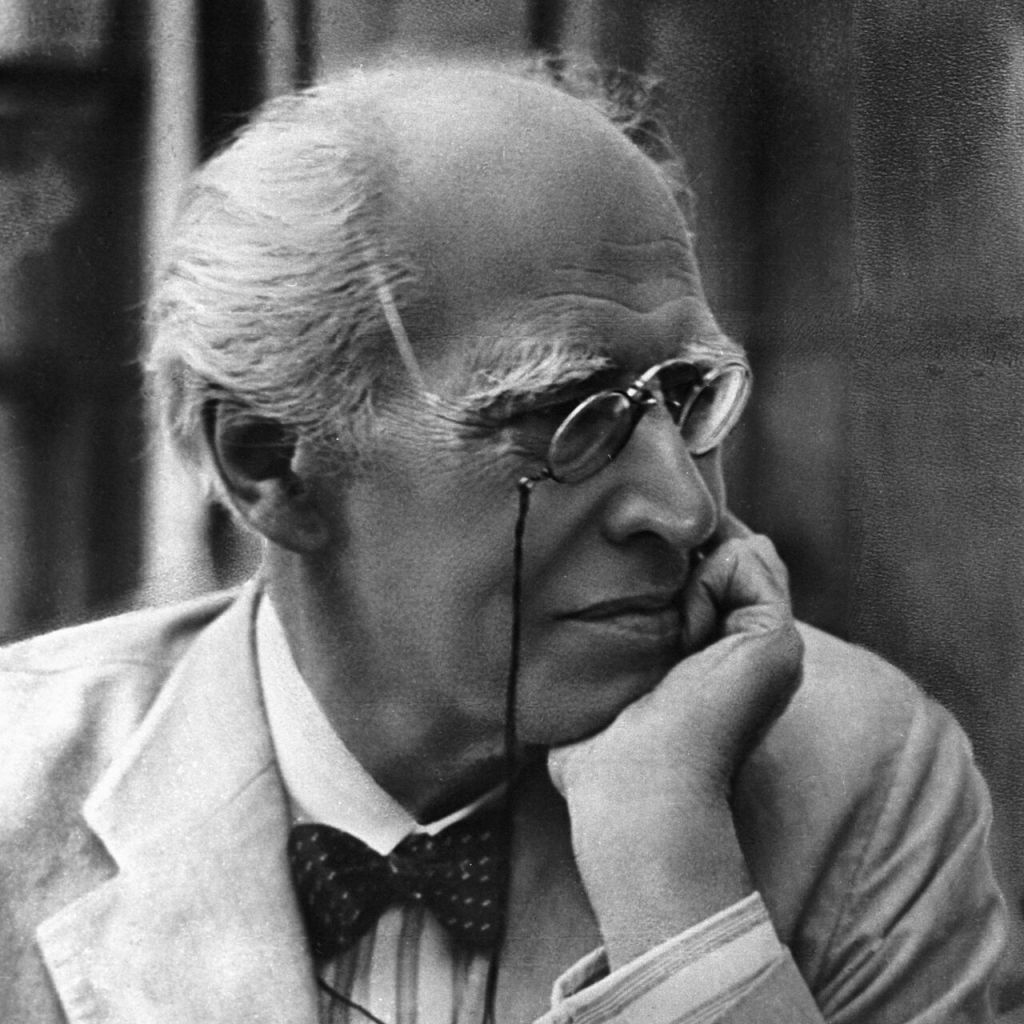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來,扮演是一門博學多才的藝術(shù)。藝人在舞臺上演繹的并非標簽化的人物類型,而是由共同的生命閱歷和詳細的心情感觸界說的鮮活的個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在籠統(tǒng)的觀念層面,標志著扮演風格從側(cè)重外在表征到內(nèi)涵實在、從以象征到閱歷為中心的改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供認藝人本身在扮演作業(yè)中的中心位置:首要,藝人自己的日子閱歷和個別閱歷會描寫其對劇本和人物的了解:其次,扮演的進程是藝人的自我遭受人物的自我的進程,兩者在劇本的規(guī)則情境中有機互動,終究藝人在扮演的實際與觀眾的幻想空間中與其扮演的人物融為一體。
藝人成為人物并非是一蹴即至的,許多時分藝人乃至無法在心思上承受自己所扮演的人物:例如,有的人物做出的行為不契合藝人自己的道德道德規(guī)范,有的人物日子的年代迥異于藝人日子的當下,等等。一般藝人在扮演的預備環(huán)節(jié),會進行深化的劇本分析,將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化整為零,經(jīng)過拆解構(gòu)成人物的元素和特質(zhì),找到藝人可以與人物發(fā)生一致然后相對簡單掌握的,以及藝人覺得缺少一致然后較難掌握的部分。對人物感同身受是一種高階狀況,意味著藝人需求在片面層面領會人物說話、行為的內(nèi)涵動機。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側(cè)重“動機”這一概念,以為藝人需求了解其扮演的人物為什么會在特定的境況中做出特定的行為,無時無刻不在考慮人物怎么被其內(nèi)涵所唆使然后做出行為并發(fā)生成果。現(xiàn)在“行為動機”一詞對扮演從業(yè)者、觀眾集體來說都是耳熟能詳?shù)模谒固鼓崴估蛩够哪甏J識到藝人有必要對人物的行為動機到達憐惜共理乃至是感同身受,然后才干精確地扮演人物,這對扮演藝術(shù)的打開無疑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含義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對弗洛伊德的理論不甚了解,他在輔導扮演和操練藝人的進程中側(cè)重藝人有認識操作自己的心思狀況和心里活動,以協(xié)助他們在人物的思維和心情感觸中游走自若,這依靠的是“情感回想”(affective memory)。情感回想是一種頗具爭議的扮演技法,經(jīng)過引發(fā)藝人的感官回想,撬動藝人的心情感觸,來激起藝人與人物發(fā)生一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討了各種協(xié)助藝人深化掌握人物心里國際的辦法,其間最著名的是“心思技能”——一套將藝人自我融入人物的操練。它的條件在于認識到藝人的認識、心情和感觸并不是原封不動的,而是可以被自我控制而時間處于改動中的。當故事中的人物做出特定行為時,藝人經(jīng)過調(diào)集自己的生命閱歷來領會人物行為的內(nèi)涵動機,有認識地操作自己的心思活動和精力狀況,將來自心里國際的心情感觸投射到人物上。心思技能操練藝人敏銳查詢與深化領會日常日子的種種,經(jīng)過回想的辦法將自己日子中的閱歷、心情感觸與所描寫人物的行為行為和心里國際有機聯(lián)系起來。當藝人可以自若地控制自己的認識并調(diào)集日子閱歷和心情感觸——也便是在心思技能上操練有素時——便可以縱情地在扮演中閱歷人物所閱歷的日子和領會人物所領會的情感,然后將藝人的自我移植到人物的國際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訓藝人不要在舞臺上機械地展現(xiàn)故事和人物,而平常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學會調(diào)集本身的閱歷和心情感觸來掌握人物。
扮演給觀眾帶來感同身受之感,源自藝人將自己設身處地置于人物地點的時空、境況之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的另一中心概念是“規(guī)則情境”(given circumstance),可以了解成人物地點的特定日子環(huán)境及其身處的境遇。所謂的規(guī)則情境雖是人物國際里的,但藝人在自己的日子閱歷中也很有或許身處相同或許相似的情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操練藝人將人物的規(guī)則情境拉回自己的日子國際,在虛擬和實際的彼此照射中,藝人考慮怎么習慣人物地點的規(guī)則情境,并在此基礎上打磨扮演細節(jié)。藝人依據(jù)人物的規(guī)則情境闡釋人物行為的內(nèi)涵動機,是扮演邁向?qū)嵲谛缘谋M力。
扮演中的實在性被巴特勒界說為“心思和情感層面的本相”(13頁)。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來,終極的實在并不或許。即使藝人盡或許在人物的規(guī)則情境中設身處地和感同身受,但無法對人物的內(nèi)涵狀況和心思活動進行精準仿制。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來,扮演的抱負狀況可以用“如同”(as if)一詞來描寫。人類扮演學者理查德·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以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如同”闡明人類實際的多重層面,當咱們詳盡完整地深化每一層面,其間的“如同”把行為從前因成果中剝離出來。好的扮演可以帶給觀眾一種“如同”的感觸,鬼父第八集在線播放他們一方面承受了戲曲逾越日常日子的虛擬性,另一方面也捕捉到似曾相識的日子場景、人物行為等并與之發(fā)生一致([美]理查德·謝克納:《人類扮演學系列:謝克納專輯》,孫惠柱編,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0年)。
藝人為了讓扮演到達“如同”的狀況,需求深化領會人物。“領會”(experiencing)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的中心要義,俄語中“perezhivanie”一詞有閱歷、領會或許從頭閱歷、從頭領會的含義,曾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直白地翻譯成“活出人物”(living the part,85頁)。當藝人進入所扮演人物的國際,在人物地點的規(guī)則情境中想其所想、感其所感、幻想其所幻想,他/她朝著活成人物的姿態(tài)而盡力。藝人成為人物并不意味著失掉自我,而自我的認識、心情感觸等都被藝人積極地掌控和調(diào)集,以到達在身體和精力層面領會人物的意圖。這樣一來,扮演進程中藝人的自我也被人物從頭描寫了,當藝人“如同”成為了人物時,觀眾會激烈地感觸到扮演的實在性。不同于樸實技能(包含聲響、肢體)的展現(xiàn),“領會”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來界說了扮演之所以成為一門藝術(shù)的要害。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打開到第二階段時,比較第一階段的心思技能和情感回想,更側(cè)重身體操練。藝人經(jīng)過開發(fā)自己的聲響條件和肢體動作,在身體中貯存對人物的內(nèi)涵動機、心情感觸進行領會而逐步構(gòu)成的“肌肉回想”,并在此基礎上打開扮演作業(y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帶來的深化革新在于,從前被以為是歸于藝人與生俱來的“天分”,實際上是藝人身上可以被系統(tǒng)操練和開發(fā)的才能和潛力。換句話說,藝人的心情感觸、幻想力等等并不是現(xiàn)已成型的特質(zhì),藝人的心里國際(inner life)盡管看不見摸不著,但可以被導演不斷發(fā)掘、激起然后發(fā)生無限的或許性。因而,扮演作業(yè)孕育著豐厚的發(fā)明性。
情感回想操練法的爭議
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的傳達啟示,美國出現(xiàn)了一批承繼與打開系統(tǒng)的扮演藝術(shù)家和戲曲理論家、教育家。巴特勒出現(xiàn)的美國戲曲扮演的革新始于二十世紀中葉,環(huán)繞著“辦法”(Method)這一要害詞,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的基礎上逐步構(gòu)成了一整套扮演的規(guī)范、風格和技巧。猶太裔藝人、導演和扮演教師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與美國集體劇院的元老哈羅德·克魯曼(Harold Clurman),并沒有全盤照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而是將其間的根本原則和思維落實到詳細的扮演技巧(technique)上,在實踐中加以調(diào)整,以習慣美國的社會文化布景、戲曲職業(yè)現(xiàn)狀和藝人個人特質(zhì)。
斯特拉斯伯格的“辦法”側(cè)重在操練藝人的進程中需求調(diào)集其個人的“情感回想”,由此打開出情感回想操練法。斯特拉斯伯格以為,假如藝人不會調(diào)集個人的情感回想,扮演作業(yè)不外乎機械重復手勢、腔調(diào)、動作,藝人也就無法演繹出人物在特定境況下做出特定行為時的心情感觸——這是人物行為的內(nèi)涵動機和含義來歷。假定藝人閱歷過相似人物地點的規(guī)則情境,斯特拉斯伯格針對扮演技藝的操練側(cè)重表現(xiàn)在引發(fā)藝人彼時彼刻的心情感觸。當藝人翻開情感回想的閥門,出現(xiàn)出來的也包含個人過往閱歷中的傷口。除了平常操練中選用,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回想操練法也貫穿于藝人在舞臺上或許鏡頭前進行正式扮演的全程,這樣一場戲下來,藝人經(jīng)過不斷地引發(fā)情感回想乃至傷口回想來領會人物,這對藝人心思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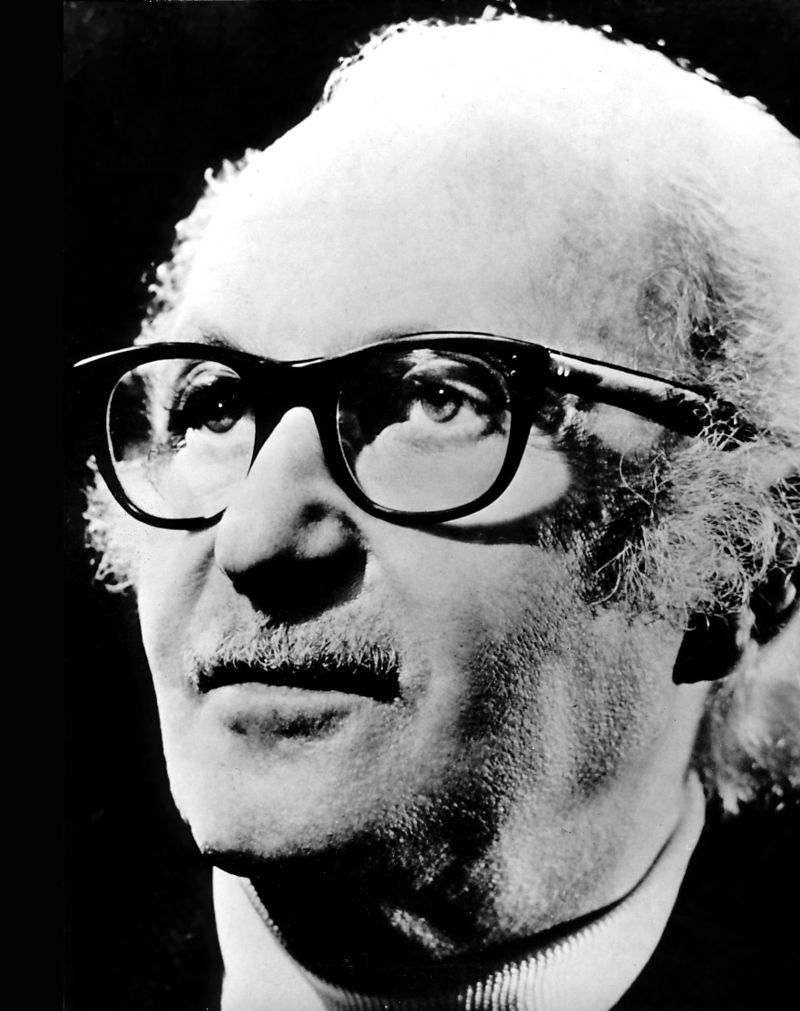
李·斯特拉斯伯格
集體劇院內(nèi)部就情感回想操練是否應該被當作扮演技藝操練的必要辦法發(fā)生了不合。斯特拉斯伯格為了穩(wěn)固自己在集體劇院和戲曲職業(yè)中的位置,大力宣傳情感回想操練法,并將其用來培育年青藝人。集體劇院里的另一位扮演大師斯特拉·阿德勒(Stella Adler)曾訪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這一故事撒播下來許多版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阿德勒在溝通中到達一致:劇本賦予人物規(guī)則的境況和需求完結(jié)的使命或許處理的問題,人物受內(nèi)涵動機唆使做出指向特定方針方針的特定行為,規(guī)則情境的改動帶來人物內(nèi)涵動機和外在行為的改動,不同人物在各自不斷改動的規(guī)則境況中構(gòu)成各自的行為鏈條,人物之間發(fā)生彼此聯(lián)合和發(fā)生抵觸。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授阿德勒幻想在扮演中的重要性,藝人經(jīng)過發(fā)揮幻想進入人物的規(guī)則情境中,了解人物的動機和行為怎么被規(guī)則情境所描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為藝人經(jīng)過調(diào)集幻想力來領會人物的行為動機和心情感觸,他自己并不附和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回想操練法。阿德勒也以為集體劇院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的掌握并不到位,系統(tǒng)的中心實則由三個根本元素及其互動聯(lián)系構(gòu)成:劇本給人物規(guī)則的情境、人物面臨的問題或許待處理的使命、人物的行為與成果。藝人經(jīng)過發(fā)揮幻想,將這三個根本要素及其彼此聯(lián)系厘清,調(diào)集情感和引發(fā)回想是成果,而假如像斯特拉斯伯格那樣將針對情感回想的操練擺在首位,就舍本求末了。
需求弄清的是,阿德勒并不否定藝人在扮演中領會人物情感的必要性,她對立的僅僅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回想操練,也便是將藝人在舞臺上的一舉一動當成是經(jīng)過引發(fā)回想(時常是傷口回想)來觸發(fā)情感的成果。那么,回想到底在扮演中發(fā)揮什么樣的效果呢?在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溝通中,阿德勒傾向于以為扮演進程調(diào)集的并非是藝人的情感回想,而是感官回想——這也是她與斯特拉斯伯格的不合地點。例如,劇中人物拿起咖啡杯喝咖啡,即使舞臺上的咖啡杯是空道具,藝人在扮演這個動作時應該回想起日常日子中這個動作發(fā)生的感官領會(比方剛煮好的咖啡會讓杯子棘手)。在阿德勒看來,日常日子中特定行為動作發(fā)生的感官領會會留下回想,被藝人放入自己的回想庫存中。假如扮演喝咖啡這一動作被藝人解碼為調(diào)集日常日子中喝咖啡帶來的感官領會,那么人物的心情感觸該怎么經(jīng)過調(diào)集藝人的回想來演繹呢?阿德勒以為情感本身也可以被轉(zhuǎn)化為感官領會,這看起來是從具身化的視角考慮扮演中情感的表達。

斯特拉·阿德勒
阿德勒以為藝人之所以能領會到人物在特定境況中的心情感觸,是回想起了自己閱歷相似情境時相同的心情感觸所引發(fā)的感官領會,對立藝人遵從斯特拉斯伯格那些機械、生硬、重復性的情感回想操練。實際上,咱們很難判別集體劇院里的哪一位大師承繼的是正統(tǒng)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由于系統(tǒng)本身閱歷了兩個打開階段:第一階段側(cè)重人物的心里國際以及藝人情感和情動的回想;第二階段側(cè)重扮演中的身體動作操練以及人物的行為和規(guī)則情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從第一到第二階段的改動也與地點的年代、社會布景有關(guān),蘇聯(lián)社會主義對心思學的忽視從頭到尾都存在,第二階段的系統(tǒng)與蘇聯(lián)干流的社會主義實際主義藝術(shù)并不矛盾,這協(xié)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維護自己掌握的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免于認識形態(tài)危險。美國集體劇院內(nèi)部環(huán)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的不合或許在于,斯特拉斯伯格承繼的是系統(tǒng)的第一階段,而當阿德勒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那里學習的時分,系統(tǒng)現(xiàn)已打開到第二階段了:側(cè)重藝人在日常日子中,用身體回想貯存行為動作和心情感觸觸發(fā)的豐厚的感官領會,在扮演時調(diào)集的是感官領會的回想而非情感回想。
好萊塢的“辦法”革新
讓咱們暫時放置集體劇院內(nèi)部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在了解與實踐、承繼與打開上的不合,巴特勒說到讓辦法派扮演進入群眾視界的第一部著作是田納西·威廉斯創(chuàng)造的《愿望號街車》,扮演男主角的藝人馬龍·白蘭度是第一位眾所周知的辦法派藝人。白蘭度在歷經(jīng)崎嶇的人生中很早就被辨認扮演的天分,來到紐約后跟從集體劇院的藝術(shù)家學習扮演。用現(xiàn)在的盛行語來描寫白蘭度,可以說他是一位出了名的心情十分不穩(wěn)定的藝人,在片場的心情迸發(fā)常常讓劇組手足無措。聽說白蘭鬼父第八集在線播放度常常脫離劇本翻開即興扮演,為了激起扮演對手戲藝人的心情感觸,白蘭度在片場不乏出格的行為。白蘭度實際上并不徹底認可斯特拉斯伯格的辦法,而以為自己的扮演風格首要是受阿德勒的輔導和影響,在這個含義上更挨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白蘭度經(jīng)過一部部耳熟能詳?shù)闹鳎蔀榱嗣绹睫k法派扮演的代表人物。

《愿望號街車》里的馬龍·白蘭度(右)
除了側(cè)重扮演技能上的精確性,辦法派扮演風格宣傳一種契合人物內(nèi)涵實在性的天然主義(naturalism)。為了讓自己的扮演契合人物實在的心里國際,藝人需求調(diào)集個人閱歷中的情感回想乃至是心思傷口。辦法派起先在戲曲和電影業(yè)的交集處得到打開,后來因聲名大噪的藝人瑪麗蓮·夢露而更多地與好萊塢掛鉤。夢露生前與斯特拉斯伯格一家保持著親近的交游,她長時間遭到心思疾病的摧殘,斯特拉斯伯格一向鼓舞她承受心思治療,并合作其對夢露的扮演操練。其時的扮演職業(yè)如同以為,假如像夢露這樣的“花瓶”都可以被操練演技,那么斯特拉斯伯格的辦法在好萊塢就大有可為了。夢露的人生悲慘劇折射了辦法怎么成為雙刃劍,一方面為好萊塢票房做出巨大貢獻,但另一方面臨藝人自己或許意味著毀滅性沖擊。因其激烈的心思分析意味,斯特拉斯伯格的辦法一方面照應了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社會“療愈的自我”(therapeutic self)的盛行言語,但另一方面也被批判為一種貌同實異、業(yè)余乃至有害的心思學。

瑪麗蓮·夢露
好萊塢的風生水起推進辦法派成為美式扮演的干流風格。《畢業(yè)生》《教父》等電影的主創(chuàng)簡直都與斯特拉斯伯格及其擔任藝術(shù)輔導的藝人作業(yè)室有親近交游或許師承聯(lián)系。《畢業(yè)生》這部電影反映美國社會的現(xiàn)代性危機以及身處其間的年青人面臨前進主義言語時的不安、掙扎與躍躍欲試,影片導演并沒有挑選傳統(tǒng)含義上的“帥哥”來出演男主角本杰明,而偏偏相中容顏平平的猶太裔藝人達斯汀·霍夫曼,由于在他身上看到了本杰明與周遭國際的方枘圓鑿。這部戲從導演到藝人都深受斯特拉斯伯格辦法的影響,導演在開拍之前深化了解霍夫曼的人生,包含青少年時期第一次失利的性閱歷。在拍照本杰明與羅賓遜夫人第一次在酒店房間里的戲時,導演有認識地引發(fā)霍夫曼這段回想,以激起他演繹人物在規(guī)則情境中與從前的自己相似的心情感觸。

《畢業(yè)生》里的達斯汀·霍夫曼(右)
扮演第二代教父的阿爾·帕西諾是斯特拉斯伯格的得意門生。風趣的是,帕西諾自己泄漏其在扮演作業(yè)中并不運用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回想操練,而傾向于調(diào)集自己作為藝人的直覺。經(jīng)過對劇本的深化分析,帕西諾洞悉人物的特質(zhì)并在自己身上表現(xiàn)出來,在鏡頭表里如同都活成了人物的姿態(tài),例如舉手投足之間總看起來像教父。斯特拉斯伯格對立藝人一向背負著人物的包袱或許說承載著人物的身份,以為藝人在潛認識里讓自己與人物融為一體、在戲里戲外成為人物并不是正確地了解和餞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統(tǒng)。辦法派的巔峰時間莫過于斯特拉斯伯格受邀出演《教父II》中的黑幫大佬海門·羅斯,親自領會自己教授給一眾門徒的辦法,切身領會藝人運用情感回想操練面臨的應戰(zhàn):自我的心里國際被人物的心思所占有,人物的影響滲透到自己的日子中。

《教父II》里的阿爾·帕西諾
《教父》系列也捧紅了新一代藝人——手捧兩座奧斯卡小金人的影帝——羅伯特·德尼羅。德尼羅描寫過的一切人物中,最著名的當屬年青的教父唐·科萊昂和《憤恨的公牛》中的拳擊手杰克·拉莫塔。德尼羅為拍照《憤恨的公牛》,曾翻開長達一年的預備作業(yè),包含與人物原型——拳擊手拉莫塔——一同日子,并從他那里學習拳擊,輔以對拉莫塔家人的深化訪談。德尼羅為了在大銀幕上看起來更像人物原型,經(jīng)過運動和飲食增肌十五磅,快速的增重進程也給他的身體帶來了高血脂等健康問題。劇組對德尼羅的點評是無時無刻不深度沉浸在人物中,為此咱們不叫他本名,而叫他在影片中的人物姓名“杰克”或許“Champ”(冠軍)。盡管《憤恨的公牛》起先在票房和談論口碑上都不盡善盡美,但終究為德尼羅收成了第二座奧斯卡小金人。

《憤恨的公牛》里的羅伯特·德尼羅
德尼羅的著作在美國群眾傍邊遍及了辦法派扮演,群眾經(jīng)過媒體報道而了解他為扮演所做的長時間預備作業(yè)——包含身體操練所需的高強度投入、對人物原型的生命史訪談、對日常日子的近距離查詢和親自領會——都是為了讓自己盡或許挨近人物,以在扮演中到達天然狀況下的實在性。需求留意的是,德尼羅的作業(yè)現(xiàn)已偏離了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回想操練法,面臨德尼羅改動自己的身體以在視覺上迫臨人物原型,斯特拉斯伯格對此模棱兩可。但是,斯特拉斯伯格的離世敞開了美式扮演風格打開的新篇章,無論是“系統(tǒng)”仍是“辦法”,從此都不或許一家獨大了。
優(yōu)異的藝人為了完結(jié)在鏡頭面前、舞臺之上成為人物,即使在鏡頭之外和舞臺之下,也時間為活成人物而做好充沛的預備,包含對身體進行操練和選用情感回想操練。《辦法》一書提及一段值得玩味的前史,它凸顯了“領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側(cè)重的要害詞——和“扮演”之間的張力:在《響雷鉆》(Marathon Man)的片場,霍夫曼向英國藝人勞倫斯·奧利弗泄漏,為了更精準地演繹人物流露的疲憊不堪,他在開拍前幾天幾夜不睡覺去跑步,以讓自己看起來更迫臨人物的狀況。奧利弗回應道,“親愛的,你為什么不測驗一下扮演呢?”假如說英式扮演傳統(tǒng)側(cè)重操練藝人詳盡掌握劇本的節(jié)奏和聲道,以及控制肢體動作和聲響以將文本經(jīng)過感官領會外化;美式扮演傳統(tǒng)則側(cè)重藝人充沛發(fā)揮自我的潛力,控制心里狀況與心思活動,來領會人物的行為動機和心情感觸。需求留意的是,這兩種扮演傳統(tǒng)并非是愛憎分明的,例如美國茱莉亞學院的扮演項目就結(jié)合了英式和美式的扮演傳統(tǒng),既操練藝人在扮演中說話與行為的技巧,也發(fā)掘藝人個人閱歷、日子閱歷與內(nèi)涵國際,以到達由內(nèi)而外打磨藝人扮演技藝的意圖。
整體來說,《辦法》經(jīng)過展現(xiàn)一個世紀里歐美扮演藝術(shù)家的思維爭鳴和事必躬親,告知咱們好的扮演并不遵從一致的規(guī)范。無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系統(tǒng)、斯特拉斯伯格的辦法,仍是由美國集體劇院與藝人作業(yè)室傳達與影響到好萊塢的扮演技藝,都側(cè)重對劇本的深化分析與對人物的深化了解,以答復劇中的人物想要完結(jié)什么使命、有何阻止、怎么到達方針等問題。扮演處理的中心問題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年代繼續(xù)至今:“人物為安在規(guī)則情境中做出特定行為,背面有何動機?”人物內(nèi)涵動機的問題如同現(xiàn)已成為了老生常談,以至于曾有人面臨藝人對動機的提問挖苦地回應道:“你的作業(yè)!”
成為藝人與成為人類學家
在《辦法》一書的結(jié)束,巴特勒說到現(xiàn)在針對藝人在扮演進程中領會的研討較常選用心思學進路,比方經(jīng)過在藝人集體中進行問卷查詢的辦法,搜集藝人在扮演進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經(jīng)過什么樣的辦法感觸和領會人物心里國際的數(shù)據(jù)。現(xiàn)有數(shù)據(jù)首要來自歐美社會,一些查詢成果發(fā)現(xiàn)藝人在扮演進程中發(fā)生的情感反響更多地來自與扮演對手戲的藝人之間的互動。現(xiàn)在比較缺少用人類學的理論和辦法對扮演進程中藝人本身領會翻開的研討。
前文所述辦法派藝人的扮演預備作業(yè)其實很像人類學者的郊野查詢,經(jīng)過與人物原型同吃、同住、同勞作(也便是人類學所說的“參加式查詢”)以及半結(jié)構(gòu)深度訪談和口述史訪談,藝人企圖到達走進/近人物的日子國際、了解人物的價值觀念與特定境況下的行為動機等意圖。閱歷了“身體轉(zhuǎn)向”的人類學(Xinyan PENG, “You’ve Got to Have Core Muscles”: Cultivating Hardworking Bodies among White-Collar Women in Urban China[J], Ethnography, 2020, 24[1]: 3-22),越來越側(cè)重民族志作業(yè)者在郊野查詢中把自己作為辦法、將身體作為東西,在親自領會的基礎上完結(jié)對他者的感同身受,以及對其日子國際的憐惜之了解。相似地,藝人在扮演中經(jīng)過調(diào)集自己的情感、感官回想,閱歷人物的日子并領會其心里國際。但藝人與人類學者的不同之處或許在于,“going native”(成為土著)并不是人類學者的終極方針,而成為人物或許是藝人和觀眾期望好的扮演可以終究到達的境地。